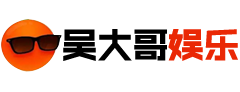截至1月25日,今年春节档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经突破了40亿元。在今年春节档7部逐鹿的电影中,张艺谋导演的新片《满江红》备受关注。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在后来的三天中,《满江红》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3亿,甚至反超位居榜首三天的《流浪地球2》。

总体来看,《满江红》具有的新颖独特的气质,其多元的类型可以让观众们在这个来之不易的档期“大年”眼前一亮,目前已经有近29万人打出了7.8分。与此同时,你更能在《满江红》中看到许多张艺谋近期类型片的影子,更是一次十分“张艺谋”的新试炼。

一种很新的“剧本杀”电影
在《满江红》的海报和预告片中,写着十二字宣传语:“大年初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用“悬疑”与“喜剧”为《满江红》定性,很显然是为了契合春节档的核心卖点。
很难用一种具体的类型来概括《满江红》,悬疑、古装、历史、感情、喜剧等多种类型在本片中杂糅,唯一鲜明的是人物的形象与充满起伏转折的剧情,与近些年开始流行的“剧本杀”颇为相似。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电影的开场,南宋末年,岳飞已亡,金使遇刺,真凶逃亡的故事背景被丝滑带出,多个核心角色带着鲜明的性格与职业标签鱼贯而出,男主小兵张大和比自己小的“三舅”亲兵营副统领孙钧也领到了“写在自己剧本最后一页”的核心任务——追查杀害金国使节的真凶。
于是主角团便展开了快节奏、强戏剧性的“搜证”环节,在一个时辰的限定时间中,伴随着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淳、舞姬瑶琴的卷入,一场场一对一、一对多的对(审)谈(讯)也紧接展开,隐藏在明线之外的暗潮也逐渐开始涌动。
整部电影就像是一场沉浸式的剧本杀,这种不寻常的电影构作与调性看似给予了观众无限“爽”感,实际上却走向一种风格化的极致内敛,密闭的空间打破了角色、作者和观者之间的界线,使得整部电影变成了一场游戏,观众获得了游戏版的观演体验,但是掌控一切的依然是张艺谋手中的“DM剧本”。
多元类型的崭新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满江红》前期的官方宣传词,还是电影的序幕介绍中,都着重于历史的底色,甚至“正剧”的质感。但是在观影的过程中,观众会接受到各种鲜明的风格的轮番轰炸,打破对于故有电影类型的认知。
出于档期与商业原因的考量,散落在推理主线一旁的还是密集的喜剧元素与商业包袱。与此同时,开心麻花演员和相声演员自带的影响力拥有强烈的现代感,无疑会与其他的要素形成强烈的对冲,然而《满江红》强烈的风格化特质即来源于各种看似不兼容的元素的杂糅。
当独具特色的河南“坠子书”与摇滚乐相结合伴随着主角团在大宅中穿行时,既有热血悬疑的张驰,又有对角色心怀鬼胎,对剑拔弩张气氛的渲染。悬疑惊悚片中标志的“突发惊吓”,昆汀式的血浆和扭曲惊恐,以及四处弥漫的阴谋与算计也与喜剧元素一样,在影片中保持着巨大的存在感。
在“惊、逗、疑”的缜密组织与高密集度的信息输出中,观众们仿佛坐着由张艺谋驾驶的过山车,在非常规的叙事连番轰炸之后,发出惯性式的笑容,但是笑容之余,又能觉出淡淡的悲凉——角色的脸谱这才被扯下,叙事的车轮继续高速向前。
电影中有两段非常具有讽刺色彩的喜剧片段:岳云鹏饰演的武义淳从得意洋洋地掏出免死金牌,到无奈地发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说过免死金牌还不能免死啊”的喟叹。
沈腾饰演的张大在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同党老友后,为掩饰悲伤而略有戏谑地喟叹:“真的干不下去了啊!”
这两段十分具有现代色彩的桥段,再加上沈腾和岳云鹏两个十分标志性的喜剧面孔,与云谲波诡的权力、杀戮和庄严的历史大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冲,在荒诞之余又透露出大厦将倾时小角色身世浮萍的悲凉。很显然,所有人都被困在了这场闹剧中,而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从“大”到“小”,看见张艺谋
不得不承认的是,自《英雄》试水古装大获全胜之余,早在《三枪》时期,张艺谋就已经尝试过古装、悬疑、喜剧等元素的杂糅,但是比起试水,《满江红》的高明之处,是张艺谋多年来的新创作、新实践甚至年轻化的转向。
《三枪拍案惊奇》剧照
许多名导在70岁后会达到新一轮的创作高峰,譬如贝托鲁奇、伍迪·艾伦,张艺谋也是在近两年进入了70+高能赛道。在《满江红》中,可以看到《悬崖之上》里终将到来的“乌特拉”(俄语黎明),更能看到《影》中的化身艺术。
《影》剧照
除此之外,靠宏大叙事与人海战术在艺术界奠定江湖地位的张艺谋,在越来越收紧的环境中却没有继续走向宏大,而是转向轻巧。从《狙击手》中细腻的人文关怀,到《满江红》中末流小兵、马车夫、打更人、舞女等历史大山中的“一粒沙”自发的前赴后继壮烈的献祭仪式与自我表达,尽显浪漫色彩。
向商业投降,背负“骂名”,还是忠于自我,除了张艺谋之外,也是不少第五代导演踯躅的问题。所以在流痞却忠勇的张大或是摇摆的孙钧之间,张艺谋也表达了自己。与此同时,《满江红》更是完成了一次用嬉笑怒骂的口吻“领进门”后,再褪去外衣,露出国族情感与记忆的高维表达,尽显反叛气质。
让秦桧成为《满江红》的传颂者,这种用反叛的、喜剧的、调侃的、游戏式的角度解构严肃的历史的年轻的、反叛的创作思维的终极目的,则是回答“为什么在吃不起饭的年代仍然需要艺术”问题的终极浪漫。
全军复诵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震撼,更在于这一幕恰恰让电影银幕发挥出了其高维内涵的宣传工具作用,使得国族的想象不仅出现在了艺术的表达中,更塑造成了银幕外的集体记忆,构成了《满江红》中最重要的一抹“红”,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不得不承认,电影在叙事、调度和表达上仍然存在值得继续推敲的突破口,但是《满江红》依然实现了多种类型、多种调性的融合,甚至在荒诞的结尾中实现了一种全新的、罕见的电影气质——既是主流的、歌颂的、英勇的,又是戏谑的、嘲讽的、隐喻的;既是一出喜剧,又是一出闹剧;既是一出历史小品,又是一部浪漫的“史诗”。